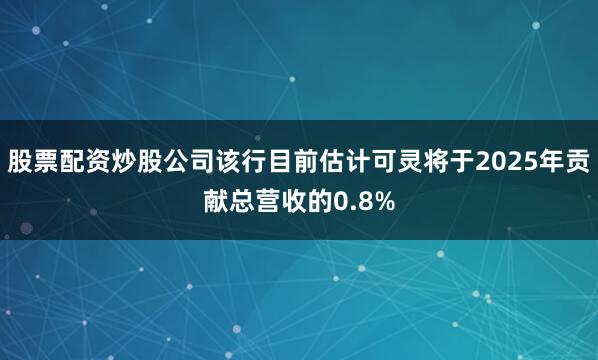本报记者田宇 肖恩楠 田建川
有人说,建筑是凝固的音乐。然而在这里,“中国民乐”与“西洋乐”竟也和谐共鸣。
漫步其中,只见罗马柱廊与镬耳山墙奇妙对话,琉璃花窗与哥特尖顶交织光影,骑楼满洲窗格与巴洛克雕花同构共韵……
这些歌唱着的旧建筑,浓缩了历史,跨越了时空,讲述着跨越三个世纪的中西文明对话故事。
这里是广东侨乡江门开平。
乱世飘摇:侨乡起碉楼
开平地处珠江三角洲西南面,潭江蜿蜒流淌穿过五邑侨乡中部。
旧时,开平曾是台山、恩平、新兴、新会四县的边界,有着“四不管地带”之称,治安混乱,土匪猖獗。
清朝顺治初年设县,定名开平,寄予了“开郡立县,天下太平”之意。
但“开平”之名并没有给这里带来太平。
19世纪50年代,开平陷入了一场“土客械斗”——本地人与客家人因争抢土地引发的冲突。开平本来地广人稀,后来人口激增,土地没有办法满足分配,于是本地人和外来客家人便打了起来,一打就是12年。
展开剩余88%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,国力衰弱,经济萧条。同一时期,美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先后发现金矿,急需劳动力的消息经回国招工的同乡在开平广泛传播,引起轰动。
贫困落后、动荡不安,于是,前往金山淘金发财,成为人们的梦想。
后来,美加两国横贯东西的铁路工地成为吸收华工就业的市场,越来越多开平乡民背井离乡、向外谋生。
到了19世纪60年代后期,开平“无侨不成村,无村不侨眷”,成为有名的侨乡。
很多华侨在海外省吃俭用,攒下的一点点血汗钱都会汇回家乡养家糊口。人们希望通过在外打拼改变家中境遇,“什么苦都可以吃,什么活都愿意干”,从不忘记“钱银知寄人知返,勿忘父母共妻房”的临别叮咛。
中国人一向有着强烈的衣锦还乡、落叶归根的情结。大多数华侨汇钱回乡或亲自回国,操办人生三件事:买地、建房、娶老婆。
他们将积蓄汇到家乡置业,带动了家乡的发展。华侨也被赋予了充满诱惑力的名字——“金山伯”“金山客”。
开平民间那时流传着一句话:“金山伯冇一千有八百。”于是,“金山伯”这一称呼,让华侨成了土匪的重点瞄准对象。
土匪猖狂到什么程度?民间有句话叫“一个脚印三个贼”,意思是华侨一踏上回乡的道路,后面至少有三个盗贼尾随。
《开平县志》记载:1912年至1930年间,开平发生过71宗较大的劫匪案件,县城曾经三次被攻陷,连县长也曾被抓走。
开平地势低洼、河网密布,一遇台风暴雨,常有洪涝之忧,由此,开平催生了一种具有防御功能的建筑形式——碉楼。最早诞生于明朝嘉靖年间的迎龙楼,最初也只为抵御洪水。后来,特殊的社会背景,赋予了碉楼更多的功能。它墙身厚,窗户小,四周墙角一般都有射击用的防卫塔——本地人称为“燕子窝”。
开平现存碉楼有1833座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,碉楼数量最多达到3000多座。
中西交响:楼影汇文明
如今,走进世界文化遗产“开平碉楼与村落”的代表性村落自力村,低矮的民居与高耸的碉楼、宽大的别墅,疏密有致地错落在稻田、池塘、河流、竹林中,别有韵味。
走近碉楼,底部是中国传统的砖石结构和方形平面。抬头仰望,顶部则造型繁复:拜占庭式的穹窿顶、巴洛克风格的涡卷纹山花、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柱式等,仿佛置身欧洲。
走进碉楼,门窗、柱头等部位的精美雕刻,既有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案、神话故事,如龙凤呈祥、八仙过海等,也有西方的植物花卉、人物形象等。
而在建筑材料上,既有中国传统的青砖、木材等,也引进了如德国的钢材、英国的水泥、意大利的瓷砖等大量国外材料。
踏进自力村铭石楼——这座美国华侨方润文所建的五层建筑,大厅里的屏风具有强烈的西洋色彩,上面却有十多幅中国诗画。玻璃是意大利进口的,而雕花是中国手工艺师傅雕刻的。走上楼,德国的古钟、日本的首饰盒,以及各种酒瓶、陶瓷工艺品等洋货静静躺在厅角的陈列柜,扬琴和留声机摆在一起……西式生活和美学元素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入华侨的生活中。
但登上房顶,只见六角琉璃瓦凉亭,五根罗马柱托起了一座中国园林式的亭阁。在这座充满异国情调的碉楼中,中国文化依然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,隐喻着游子“落叶归根”的文化眷恋。
这样中西元素的水乳交融,在开平并不鲜见。
华侨回国,带回的不仅是金银,不仅是钢筋混凝土,更将海外的美学、文化与思想融入故土。
他们将海外所见所闻与中国传统审美情趣相融合,倾注于建筑之上,使之成为留在故土的一片精神守望地。
如今,透过碉楼“燕子窝”,望见的不再是刀光剑影、枪炮硝烟,而是稻田翠色。写在上千座碉楼每个角落的侨乡文化,其生命力也正如这片翠色,生机勃勃。
在开平,另一种充满反差感的建筑形式是骑楼。
骑楼是一种近代商住建筑,最早起源于东南亚。岭南地区日晒多雨,骑楼一楼临街,建成走廊,成了造福行人的“避风港”和“遮阳伞”。楼下既可住人,也可以做商铺。走廊上方是二楼,远远看过去犹如二楼骑在行人走廊上,因此得名。
在今天的赤坎华侨古镇,游客漫步在有680多座、绵延近3公里的古骑楼建筑群中,尝“金山咖啡”、赤坎煲仔饭,看“赤坎火秀”烟花与铁花表演,乘摇橹船、坐铛铛车,感受历久弥新的华侨文化。
景区从2023年试运营以来,游人络绎不绝。古老的骑楼穿越时光,等来了更多年轻的面孔。
家书抵万金。在海外谋生的华侨心系家乡和人民,通过家书与家人联络并汇款,由此产生了一种名为“侨批”的特殊家书,也称为“银信”。这是海外华侨寄给国内亲属家眷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,“银信合一”,饱含深情。
当时,这些银信由“水客”背回家乡。当年华侨把银信寄到古镇上的各大银号,银号拆信后,支票就可以兑换成现款,再转交到收款人手上。一直以来,侨汇都是侨眷们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。
相传,很多建筑是按照当时在外华侨寄回的明信片照片建造的。在侨汇支持之下,一栋栋模仿西方建筑、中西合璧的骑楼平地而起。
漫步其中,骑楼风格不一,有罗马式、希腊式、哥特式、巴洛克式等,杂糅在一起,仿佛置身世界建筑博览园。
抬头望,女儿墙的雕塑上有许多中式建筑的元素。有象征五福的蝙蝠、寓意多子的石榴,还有预示喜上眉梢的梅花与喜鹊、象征五谷丰登的大花篮……
不只是老建筑。现在行走在广东的大街小巷,看到街边路牌、听人们讲起粤语,也会有许多神奇的叫法——商店叫“士多”,源自英文“store”;打球叫“打波”,源自英文“ball”;草莓叫“士多啤梨”,源自英文“strawberry”,等等。
华侨回乡跟乡亲聊天,有意无意夹杂的外来词汇竟成了时髦,带动了侨乡学英语的热潮,外来语慢慢地融入当地话中,直至今日成为亲切的乡音。
根系家国:建筑在歌唱
在距碉楼群十公里外的立园顶楼,祭拜祖先的神龛两侧有园主谢维立亲手书写的一副对联——
“宗功伟大兴民族,祖德丰隆护国家。”
有趣的是,上联“民”字的最后一笔斜钩起笔位置在整个字最上方,一笔出头;下联的“国(國)”字中间并非“或”,而是“民”。
在这座耗时十年、耗资26万银元、融合了《红楼梦》大观园的意境与欧美建筑风格的“中国华侨园林一绝”中,神龛上有这样两个特殊的字,寄托了园主怎样的期许?
“一笔出头,意指后辈要努力,让中华民族早日有出头之日;国中为民,代表国以民为本、民以国为家,有国才有家。”这样的解释,不免让人又震撼又感动。
把家国情怀如此厚重地融入家族血脉中,在这里并不罕见。
作为用双脚走出去“睁眼看世界”的人,华侨们对祖国落后、被西方人欺负的痛苦有多强烈,建设家乡、“振兴中华”的愿望就有多迫切。
赤坎古镇是当地两大家族在长期互相竞争合作关系中慢慢形成的。上埠是关氏,下埠是司徒氏,他们在古镇东西两端聚居发展:你建骑楼我也建骑楼,你建碉楼我也建碉楼……这种看似对抗的“军备竞赛”,实则激活了赤坎古镇的发展活力。
赤坎发明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是开平早期股份制公司之一,由关氏和司徒氏家族携手创办。1923年开始筹办,1924年投入生产发电,每天晚上6点到12点供电。1928年,开平县灵通电话有限公司也开始筹办。
上世纪50年代流行过的“楼上楼下,电灯电话”,寄托着几十年前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理想。但在100年前,赤坎的居民就开始用上电灯电话。正是两族的合作共赢,促进了赤坎的发展。
自力村铭石楼里,展示着一张过去的《华侨日报》,其中关于教育的内容占了一整版。在异国他乡的经历让华侨们深深懂得:只有科教才能兴国,只有教育才能救国。
在这样强国救国爱国的精神感召下,赚到钱的华侨们回到家乡,兴办学校,鼓励后代和附近乡民的后代接受教育。此外,他们还兴建医院等公益机构,建设家乡、造福乡亲。
而在赤坎,司徒氏在1925年建成图书馆后,来自美国的大钟敲响的洪亮钟声在赤坎古镇回荡,引起关氏家族的强烈反应。关氏也立即筹资兴建竞争性建筑关族图书馆,认为“将来图书馆落成后,可为一族之光”,并从德国也进口了一口大钟。关族图书馆大门外的对联“骨肉有情宗亲倾积愫,同胞着意书馆起宏图”,昭示出关氏以文化谋未来的决心。
通常,祖先神位都是摆放在一楼大堂,而在开平却恰恰相反,被供奉在最高层。当地人认为,这是期望坐得高看得远,“高瞻远瞩”的神位能保佑海外游子兴旺发达、平安归来。
今年3月底,立园园主谢维立先生的女儿谢美娟,携子孙三代15人回到故乡,回到儿时成长的地方。置身于父亲打造的杰作里,她回想起父亲“非常希望能回到祖国大陆置业,他非常爱国爱乡”。
“红棉花开的时候,我就想回家了。”乡音无改鬓毛衰,今年已经90岁的她形容这次回家是“美梦实现了”。
离开自力村时,记者注意到村口的大榕树枝繁叶茂。榕树是侨乡的风水树。在生长过程中,枝干上会生长出许多气生根。这些气生根从枝干垂下,接触地面后就转化为支柱根。根须深深地扎在泥土里,支撑庞大的树冠,吸收水分和养分。
一代代侨民就像这榕树,枝干生生不息地生长,子孙一代代繁衍生息。但他们无论身处何地,枝条伸向多远,根系都牢牢扎在家乡的土里。
老榕树在村口守望着老建筑,也在等游子们回家。
发布于:北京市盛达优配app-正规配资炒股平台网址-低息配资开户-专业配资公司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